编辑|晶晶
排版 | 苏沫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推出《四味毒叔》的第二期视频播客,与刘震云老师展开这场对话,起初是因为他的长篇新作《咸的玩笑》面世,但这不仅仅是一场新书对谈,更是一次深入创作腹地的“盐分”提取。
刘震云与老友宋方金、史炎、梁彦增一起,掰开揉碎了书中那些令人过目难忘的灵魂:琢磨秦始皇的裁缝、窥探路人隐秘的糖葫芦摊主、在泰山顶上追问人性秘密的黑猪、吃百家奶长大的智明和尚……他们不只是纸上的人物,也是“困在时空深处”的我们。
对谈更触及了刘震云独特的结构哲学——人生过不去时,要学麦子“装死”,等待春天成为“春芽”;而再艰困的死局里,总有一个被善意预留的“活扣”。
刘震云的深刻,总包裹在质朴的幽默里;宋方金的机锋,常在精准的捧哏中闪现;梁彦增的自嘲与真诚,则提供了另一种进入文本的路径。他们的交锋与共鸣,都在由史炎主持的这场关于“玩笑”的讨论中,格外严肃,也格外真切。
最终,对话落回一个朴素的共识:一本书的完成,不在作家搁笔时,而在读者读完后。
生活是咸的,文学也是。好在,总有一个“活扣”藏在书页之间,等你找到。
史炎:欢迎大家来到《不开玩笑》,我是主播史炎。本期节目由《不开玩笑》《四味毒叔》《新周刊》联合录制播出。我真的太激动了,按照惯例,这样我们还是先请两位老朋友,我们的主播上场。让我们掌声有请宋方金、梁彦增。
宋方金:小梁刚才还想堵在我前面,找不对自己的位置。
梁彦增:主要是您没明示我到底是什么位置。
史炎:是,我们今天三位主播,我们今天三个都是有自己的任务的,我代表《不开玩笑》。
宋方金:我当然代表《四味毒叔》。
史炎:那么小梁你……
梁彦增:我本来是想代表《不开玩笑》的,这不你先代表了吗?那我……
宋方金:你想代表作家?
梁彦增:您不会给我实际上是这种定位吧?那肯定不敢。
史炎:是的,代表一个文学爱好者?
梁彦增:对,读者。
宋方金:《读者》?《读者》你也代表不了,那个杂志发行量很大。
梁彦增:我代表长发黑龙江人吧。
史炎: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了,让我们用一次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也是大家非常喜爱和熟悉的刘震云老师。
刘震云:第一次来史老师的主场。
宋方金:很简陋是吧?
刘震云:这个屋子你要说特别富丽堂皇…也成立。但最“成立”的还是今天到场的各位朋友。周五,下雪,大家还要赶来。
刘震云:梁彦增老师的脱口秀我也看过很多,但是基本上是在网上,因为我知道到现场的话得买票。
梁彦增:有哪位好心人出一张?
刘震云:方金老师是我的老朋友,认识二十多年了。我是看着他的书长大的,我写书他也给了我很多教诲。
宋方金:但你从来也没听过。
刘震云:听的话,效果可能更好一些。其实这本书上在封皮上印着一句话,《咸的玩笑》是世上有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完。
史炎:对。
史炎:刘老师的新书《咸的玩笑》和我们节目《不开玩笑》在名字上很有缘分。
宋方金:刘老师就是为了蹭咱们的流量,才起的这个名字。
刘震云:一开始这书想叫《不开玩笑》。但宋老师说,那会侵了史老师和梁老师的权益。这两位都是狠角色,稿费可能不够赔。那就改吧。改什么名字呢?是宋老师出的主意,叫《咸的玩笑》。
宋方金:在《咸的玩笑》之前,我还想过叫《一地玩笑》。但有一位年轻的作家,也叫刘震云,写过《一地鸡毛》。
刘震云:啊,不熟。
宋方金:噢,不熟。那位刘震云告诉我,一个作家不能占别人的便宜。《一地玩笑》占《一地鸡毛》的便宜,不行。即便我就是那个刘震云,也不能占自己的便宜。他还说,当年写《一地鸡毛》后,有编辑让他接着写《一地鹅毛》和《一地鸭毛》,凑个“三毛”系列。刘震云回答说:我也不能占三毛老师的便宜,因为三毛老师也并不比史、梁这二位老师软弱。所以,最后还是叫《咸的玩笑》。
宋方金:这名字在刘老师作品系列里很少见。刘老师很少用“的”,因为叫“什么什么的”,这个“的”就把速度降下来了。之前只用过一次“的”,是《吃瓜时代的儿女》。这次起名有何缘由?
刘震云:当初我和宋老师及出版社的朋友也商量过。这书到现在可能出版有一两周了,我看在京东、当当都是排名第一。
梁彦增:必须的。
刘震云:都排第一,不厚道吧?
宋方金:是这样刘老师,第二名是《一句顶一万句》——巧了,作者也叫刘震云。
梁彦增:宋老师,我跟您真学东西。认识您之前我简直在乱说。
宋方金:怪不得您没有股份。
梁彦增:真是应该的。
刘震云:作者给作品起名字,其实对作者来讲是个非常大的难题。一本书三十多万字,名字就几个字,这几个字你怎么能够高度地概括和提炼这个书的内容,我觉得也是个学问和智商。但我觉得,任何古今中外的书名都无法真正概括这个书的内容,因为提炼就是把复杂变简单。书里有句话:“凡是把复杂变成简单的人,都居心叵测。唯一的活扣,是把简单再变成复杂。”但是把复杂变简单容易,把简单再变复杂,就没那么简单了。现在网上有几百个主播在卖这本书。我想,为什么?或许因为卖它能赚钱。为什么能赚钱?是因为我写得好,也可能因为读者看了有感触。
很多人问,为什么叫《咸的玩笑》?有读者总结——因为所有人都有咽到肚子里的眼泪和玩笑。当眼泪和玩笑一勾兑,玩笑就变成了咸的;世界上所有人都让我加油,但刘震云在扉页上写的是:“大家辛苦了”。以上这两个总结,恐怕以我的智商达不到。
宋方金:什么是“咸的玩笑”?我举个例子:刘老师这本书上市一周,卖了梁彦增一辈子卖不出去的量。
梁彦增:我就是那个“咸的玩笑”,我写书就是“闲”的。
宋方金:“咸的玩笑”都是酸涩的。
刘震云:生活开的玩笑,有时比平常的笑话要严重得多。打比方说我和方金闹了矛盾,顶多不理他就完了。但如果你和生活闹矛盾,生活再收拾你,你难不成还能不生活了吗?每个人心里都有无法言说的“咸的玩笑”。这种玩笑有时会透露出一点异彩。每个人都有异彩,但有时候,那异彩是咸的。
宋方金:这叫“挂彩”。
梁彦增:我之前看《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觉得找到人说话好像特别重要。但是在看《咸的玩笑》的时候,发现好像找到人说话也不太解决这个问题,书中主角杜太白热爱文学,延津本地人就觉得他是个雅人,是个很有文化的老师,他通过这个优点和长处在延津还算受欢迎,也赚到了一些收入。但当他和延津本地人交流时,人们总回他一句“听球不懂”。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人是无法选择跟人说什么的。你是一个被人“听球不懂”的人,这是一种宿命,或诅咒,也可能是恩赐。我愿意像杜太白那样,带着这种恩赐或诅咒生活下去。这是一种很酸楚的鼓舞。
宋方金:我听了梁彦增这么多年的话,只有今天这段是“听球不懂”。
梁彦增:我求求您了。
宋方金:你以前那些我倒都懂。最早在抖音刷到你,总是在说些“浅显”的话,然后突然来一句“到我的主页来看看”。我今天倒想看看你的主页。
梁彦增:我不务主业。
宋方金:赶紧弄主业去。
刘震云:主人公杜太白这个名字,也是有来源的。他小的时候,像咱们宋老师一样,爱写诗,就让小学老师给他重起个名字。他原来叫“杜有才”,想着要起个文雅一点的,老师就说你正好姓杜,中国两个大诗人一个杜甫一个李白,要不把他俩都占了得了,就叫“杜太白”。还有一个文中人物是在农贸市场卖水产品的,养了一只小白鼠,这个小白鼠名字叫阿基米德。
史炎:是。
刘震云:这些生活中的异彩,有可能它就在我们身边,就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可能过去在文学作品里边还没有呈现这个,那这本书把它给呈现出来了,那呈现出来的话,这个作品它可能也许会具有独特的价值。比如说为什么一个人要从事文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人有时候特别地匆忙,有时候事儿裹着人往前走,有时候这个道理就忘了,这个事为什么这么发生?两人为什么这样闹崩了?这接着为什么就离婚了?到底因为什么?有时候这个错综复杂的原因就来不及分析。但是文学需要把这些道理一点一滴给分析清楚,这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像方金说的,人是孤独,但人找不着人说话也孤独,那就证明不是人的孤独,是话的孤独;但其实比话更重要的孤独又是道理的孤独。你比方说史老师他根本听不懂,梁老师也听不太懂,宋老师听懂了假装没听懂,这个道理它就很孤独。但是我想我说这些,在座的各位朋友都能听得懂。大家的水平比他仨还是要好一些。
宋方金:当然,否则大家怎么会来到这里呢?刚才刘老师分析了杜太白这个名字。那么这本书它为什么是“咸”的玩笑呢?实际上是写了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心情的颠沛流离,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杜太白是个失败者。但杜甫和李白这两个人可不是失败者,虽然说生活中也有不如意的地方,但是这两个人有共同点,就跟咱们都是男的和咱们都是作家一样。李白和杜甫的共同点:一,都是诗人。二,两人都登过泰山。那么在刘震云老师之前所有的小说中都有个共同特点,我把它命名为“母亲河叙事”。中国两条母亲河,一条黄河,一条长江。那么刘老师原来的小说主要集中在黄河边上,写逐水而居的这些人。那么到了《一日三秋》,刘老师的野心略大,觉得那母亲河它是两条河,咱不如把它都写了。所以说你们去看,《一日三秋》里边写了武汉的长江和西安的黄河。那在母亲河叙事之后,《咸的玩笑》这本书叫“父亲山叙事”。刘老师第一次写山写的就是五岳之首泰山。李白和杜甫这两个唐朝最伟大的诗人都登过泰山,但是两人截然不同。
宋方金:这本书结构惊人:〈正文〉两千字,〈题外话〉三十六万字,〈正文二〉两千字。为什么是“题外话”?因为杜太白遭遇的林林总总,看似都是人生的“题外话”。真正的觉悟只在瞬间,而人生,大多由“题外话”构成。
刘震云:书里有个裁缝老殷。他一边做衣服,一边琢磨:秦始皇是怎么生活的?为什么死后有九千多个兵马俑陪着?他是怎么活的?我怎么活的?他怎么死的?我将怎么死?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还有一个卖糖葫芦的老辛。卖糖葫芦是副业,主业是琢磨每一个路人的隐秘,表面上都道貌岸然,到底你肚子里那个男盗女娼是什么?巴尔扎克说,文学要写一个民族的秘史。秘史在哪?就在每个人心里。
宋方金:很多年前我跟刘老师在一块的时候,有一天上班,刘老师说,方金,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没睡好。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表哥给我打电话,昨天晚上11点多了,老家表哥打电话:“刘震云,你睡着没有?”刘震云:“我睡着了。”他表哥很激动:“现在萨达姆都被绞死了,你还在睡觉?”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得以存在的真正原因。
史炎:对。
宋方金:如果一个裁缝他就只管新衣服,一个厨师只关心炒菜,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所以说一个人想把杜甫和李白结合在一起,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这就是创新的动力。
史炎:对。
刘震云:方金老师说出了另外一个道理,就是因为好多人说我的小说很幽默嘛。说这个小说读着读着就笑了,读着读着又哭了。这个哭可能因为确实是“咸的玩笑”。其实我小说的句子的话,方金也曾经给阐述和指导过,非常质朴,没有任何一个是说要逗大家笑的。但读者为什么笑?是因为结构。像刚才方金说李白和杜甫都登过泰山,并发出了极大的感慨,包括“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因为杜甫那个时候很年轻,他喜欢直抒胸臆。但是过了一段,他经过那么多的战乱,就开始写另外一种……
宋方金:“万里悲秋常作客”。
刘震云:还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个跟“会当凌绝顶”一对比,就好像两个人写的。所以刚才方金老师说得特别对,为什么大家那么多的读者朋友对书中主角杜太白这个颠沛流离的过程有感触?因为每个人都在颠沛流离,没有一个人都是一帆风顺的。“一帆风顺”是个形容词,但其实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我觉得包括我在内所有的人,大多数情况都是磕磕绊绊的。那当你遇到绝境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喜欢这本书的原因,里边把那些家常的道理讲得很深刻。
史炎:是。
刘震云:书里春芽说:世上最好吃的面粉是白面。麦子是所有庄稼里生长时间最长的,历经秋冬春夏,它经历过生死。冬天麦苗看似死了,春天又长出新芽——“春芽”。这棵麦子还是原来那棵吗?不是。麦田还是原来那片吗?也不是。所以过不去的时候,你就“装死”。给时间一点时间。唯一不变的是变化,要相信客观的春天会来。
宋方金:人要活,你得装死。像麦苗一样,冬天被石碾压过,春天就萌发得更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刘震云:(聊到书中黑猪)……杜太白小时候家里有头黑猪,是他母亲养的,眉间有一颗红痣,在猪还没杀的时候,父亲就为了讨好人都许出去了。猪很愤怒:我还没死,身上的东西就被分完了?结果杀猪时,猪就挣脱麻绳跳井自杀了。二十年后,当杜太白在泰山顶上想轻生时,猪突然出现,就问了他三个问题:
第一:“二十年前有个小孩,坐猪圈上拿鞭子抽我,是你吗?”“是。”“为什么抽我?”“没什么,闲的,抽着玩。”猪说:“这还有天理吗?”
第二:“你爸在家厉害吧?”“厉害。”“有一天夜里,他喝酒回来,没进屋,到猪圈跟我睡了一夜,还哭了,为什么?”“那我不知道,我从来不相信我爸会跑到猪圈里跟猪睡一夜。”
第三:“当时杀我,脚上绑的绳子是活扣,如果是死扣的话我跑不了。是谁系的,你知道吗?”杜太白依旧答不上来。
猪说:“三个秘密,两个没解开。看来世上有两件事不能直视:一是太阳,太亮;二是人性,太黑。”说完跳崖,后又飞起,化作凤凰,对杜太白说:“杜老师,他乡遇故知,也算缘分……这世上并无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这一段是结构。
宋方金:这其实也是三个“咸的玩笑”,且我认为第三个最具深意:不要以为生活给的都是死扣。在最艰难的死局里,可能有人给你留了一个活扣。读完这本书,我们都要找自己命里的那个活扣。
刘震云:我替方金总结:生活有活扣,活扣在《咸的玩笑》里。
刘震云:(谈到书中智明和尚)……智明和尚这段,很多人看哭了。他俗名长顺,泰安人,不足七月生在麻将桌下,吃百家奶长大。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铁匠,后爹待他不好,常叹其是“无用之人”。后来他去投奔舅舅,但家里舅妈冷待他。因为舅舅是泰山的挑夫,要上山送菜到普照寺,他就跟着一起去了,听见和尚念经,出来对舅舅说:“舅舅,我知道该干什么了——我要当和尚。”舅舅问为什么,他说:“寺里这么多人,都离开了爹妈,所以大家都一样。”七十年后,他成为了延津鸡鸣寺的高僧。舅舅拄拐来看他,临走时,他送舅舅到山下,脱了衲衣跪下:“舅舅在上,受长顺一拜。”舅舅扶起他:“长顺,舅舅是想帮你,但我一个挑夫有心无力,才使你到这般地步。也别怪你娘和后爹,他们都已经死了,你心里边也原谅他们吧。”他说:“舅舅,他们是我的恩人。没有他们,我不会悟道;不悟道,我就成了跟他们一样的人。”舅舅半晌道:“这话刻薄,但也是实情。那既然这样,把你舅妈也算进去吧,她也已经死了。”……这也是个结构。智明和尚从泰安到延津出家,杜太白从延津到泰安开饭馆。有时没联系的事,内部血脉却相连;有时有联系的人,反而毫无瓜葛。像方金老师,认识了二十多年,永远是我的老师和好朋友。
宋方金:我以为只有前半句呢。
梁彦增:我以为有反转呢。
刘震云:这本书里的人物都困在各自的“边”里。这个“边”可能你说的是国界、是地域,更重要的一种是认识,因为大家这个社会形态不同,经济形态也不同,生活习惯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信仰也不同,这都是边,正因为这些边,就产生了纷争。
宋方金:这本书最伟大的地方是创造了世界文学的一个新领地——“困在时空深处的人”。以前文学要么是“回故乡”,要么是“去远方”。刘老师在《一句顶一万句》里把这两者结合了。到了《咸的玩笑》,他写的是根本走不出去的人。杜太白被困在延津,被困在他生命的时光深处,一生中去得最远的地方竟然是大山东。他困在时空深处,他没有遇见《一句顶一万句》里杨百顺遇到的传教士老詹。那这样的人的命运是什么?所以说这本书回答了疫情之后,全人类从宗族社会转入社区社会,如何回答我们的现代性议题。我们都是杜太白,往前走不动,往后回不去。
刘震云:(谈及书中人物起名)……杜太白的话给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起名字,儿子的话就叫巴黎,然后的话就是女儿叫纽约,还有侄子是叫伦敦。有人就是读到这儿他老笑。我们村我表弟给他三个孩子起名字,就是巴黎、纽约和伦敦。有时候包括到其他地方去交流的时候,我说我们村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们村。别人是个形容,但我们村确实每天这个巴黎、纽约和伦敦就在村里光屁股跑。
宋方金:我是山东青岛人,我们村起名字也是这么起,但是我们村起的名字是小青岛、小潍坊、小东营,没出过省。这就是区别,人家胆大包天,直接出境了。这说明一个伟大作家的诞生,他的生长环境很重要。杜太白一辈子没走出延津,最远只到山东,但他心里装着巴黎、纽约、伦敦。刘老师常说他是村里最不幽默的人,其实他是生活的搬运工。那些幽默都来自生活,编是编不出来的。
刘震云:我得空去青岛边的宋家庄看看,也请宋老师来我们村。咱们可以组团互访。
宋方金:咱们这两个山东人与河南人,就像《鲁豫有约》一样,孔子当年就做过一期——驾车到河南,回来他就写了《论语》。
刘震云:智明和尚有段话很妙。我在书中和他对话,问他说:苦海无边,佛法也无边,哪个更无边?他答:“有边更无边。”因为智明和尚知道我曾写过《温故一九四二》,里面有写到一九四二年,因为一场旱灾死了三百万人,他说:我说句不该说的话。我说:大师请明示。他说:不是死了三百万人,是一个人死了三百万次。我一听这话如醍醐灌顶。归根结底,人被困在了“边”里。这个边可能是国界、是地域,更重要的一种是认识,因为这世界的社会形态不同、经济形态不同、生活习惯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信仰也不同,这都是边。地球上有近200个国家,80多亿人,但终归地球在宇宙里不过就是个小黑点。当我最终来到泰安,看见不同国度、肤色的人熙熙攘攘,才明白:正因为“有边”,才有纷争。最后一章,我独自坐在餐馆,旁桌好友干杯。我也举起杯子,跟着干了一杯。这就是结尾。
刘震云:一个作品的完成,不在作者写完那一刻。唯有读者读完有了感悟,甚至感悟比作者更深,作品才算真正完成。这才是作者的基本价值。我确实得过一些奖。但最大的奖,是在高铁上、路上,被陌生人认出来,说:“刘老师,我喜欢您的书。”书是别人花钱花时间买的。若写得不好,对不起的不仅是钱,也是别人的时间。这话也与史老师、梁老师共勉。
梁彦增:一会儿门口找我退书钱,朋友们。
史炎:您真会看读者留言?
刘震云:会看。书上市一、两周了,也有很多留言。有时读者的感触会给我很大启发。生活中一些无意间的温暖,或者朋友间知心的话,都能滋养一个作者。
史炎:说到感触,我特别喜欢书里关于喝酒的那句:“少倒点、少喝点”。就六个字,很朴素,但那是真正的关心。因为如果酒已经倒满了,再说少喝点,就浪费了。
刘震云:对,这句话就是生活中那种真实的唠叨,是好朋友才会说的话。这种细节往往最能触动人心,因为它来自真实的生活。
宋方金:这就是“人间多少事,两三笑话中”。读者懂了,书才算成。
刘震云: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世上没有真相,只有角度。读者的万千视角,是作者最好的滋养。
史炎:时间差不多了。最后请刘老师与大家合影,之后是签售。
刘震云:谢谢大家周五下雪天赶来,辛苦了。
宋方金:“大家都辛苦了”——这话也是您书里写的。
刘震云:是,世界各地不同的街道上走着的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伤痕,大家都辛苦了。
广告声明:文内含有的对外跳转链接(包括不限于超链接、二维码、口令等形式),用于传递更多信息,节省甄选时间,结果仅供参考,硕谷新闻聚合所有文章均包含本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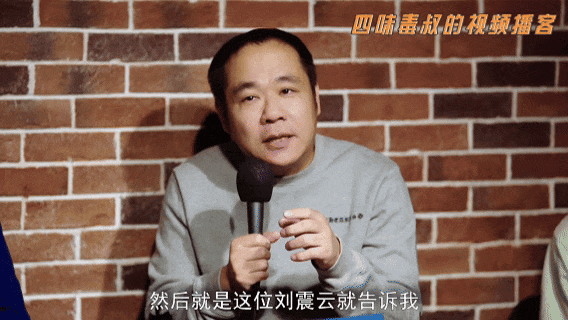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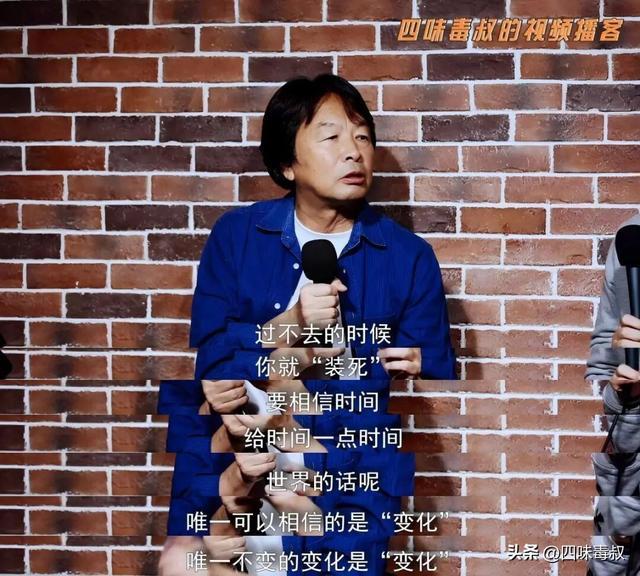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